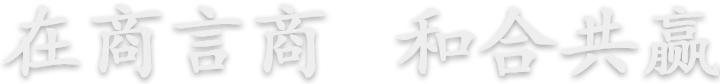
从沪深多元条例看商事调解对城市治理现代化提升
唐潮 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秘书处
2021年5月和2022年5月,上海、深圳两地间隔一年相续施行了《上海市促进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条例》(以下简称“《上海多元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以下简称“《深圳多元条例》”)。两部多元条例既是对两地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成果的立法固化,也将为推动商事调解向深发展提供规范指引。本文旨在聚焦沪深商事调解发展路径,通过对沪深多元条例解读,展望商事调解建设对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一步提高。
一、上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现状
上海作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近年来持续把高水平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2021年8月,上海市委印发《法治上海建设规划(2021-2025年)》,指出要把法治打造成上海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城市治理的闪亮名片。加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地方立法是新时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商事调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大力推进商事调解机构建设
2011年,上海率先成立了全国首个商事调解机构——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以下简称“SCMC”),拉开了上海建设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序幕。经过十余年发展,上海已设立有SCMC、上海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等多家专业调解机构,为贸易投资、金融证券、知识产权、海事海商领域的纠纷提供调解服务,商事调解的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水平得到有力提升。其中,SCMC引领发布了全国首个《商事调解规则团体标准》,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打造上海高标准营商环境做出积极贡献。近年来,为更好地服务异地当事人,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各专业调解机构创新在线调解途径,以高效、便捷的服务跨越了空间、时间的距离,拉近了当事人之间“心的距离” 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持续推动诉调对接机制建设
上海各级法院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讲话精神,持续建设诉调对接机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打造“上海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积极探索与各类调解组织的互联互通,提升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实效。自2019年成立至2021年11月,在线委派委托调解案件16万件,调解成功5.7万件。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整合资源创新社会治理,共同形成强有力的诉源治理大格局,在自贸区法庭成立涉外商事纠纷“诉讼、调解、仲裁”一站式解决工作室,携手调解机构成功调解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涉外商事纠纷。
(三)商事调解地方立法取得长足进展
上海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本市调解组织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诉调对接工作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制度文件,基本形成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在此基础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会同上海市司法局统筹推进《上海多元条例》起草工作,通过调研、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吸纳各方建议,于2021年2月26日正式通过。
《上海多元条例》的出台旨在促进和规范本市的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推进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上海多元条例》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司法调解优势互补、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对调解组织、调解员、调解活动做了详细规定;鼓励通过互联网推进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便利化。条例还鼓励国有企业通过和解、调解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消除国企参与调解的后顾之忧,助力全面推进上海国企法治建设。
二、深圳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现状
深圳与上海同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四十年来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19年,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以下简称“先行示范区”)和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设立拉开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双城记”,对我国经济向着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第15项明确提出要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健全国际法律服务和纠纷解决机制。
(一)加强商事调解组织和行业建设
2014年深圳成立了深圳市蓝海现代法律服务发展中心(后发展为深圳市蓝海法律查明和商事调解中心,简称“蓝海商调中心”),开启了对商事调解市场化运作的探索。截止2021年底,深圳已建立包括蓝海商调中心、深圳市前海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等5家商事调解组织,培养了一批商事调解员,在商事调解的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建设上取得了颇丰的成果。
2021年5月21日,深圳挂牌成立全国首个商事调解协会——深圳市商事调解协会(以下简称“深圳调解协会”),除商事调解机构外,协会成员还包括深圳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供应链金融协会等单位,推动商事调解行业走聚合力优管理之路,将充分利用协会资源探索建立行业规范标准,推积极培养国际商事高层次的国际人才,为中国调解走向世界提供深圳的方案和样本。
(二)深化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
近年来,深圳法院全面深化改革,积极推动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实现司法确认程序与纠纷多元化解的有机衔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2018年,深圳中院推行了在线解纷模式,自主开发信息化平台——深融平台,为矛盾纠纷的多元分层化解提供了条件。仅疫情严重的2020年2月份,通过深融平台在线调解8962件,打造了诉调对接的“深圳样板”。此外,深圳法院引导深圳各银行将调解优先纳入合同条款,并与街道社区联合设立非诉解纷工作站、司法确认室,实现诉调对接全覆盖。
(三)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立法
深圳不断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充分用好全国人大授予的法规制定权,出台了一批有利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地方性法规,衔接国际通行规则。《深圳多元条例》吸收了深圳多年来在商事调解建设中形成的经验成果,通过立法的规范、引领作用保障深圳深化建设多元解纷机制。条例规定了调解、仲裁、行政复议等多类型纠纷解决,优化诉讼与非诉讼矛盾纠纷化解的有机衔接,是国内同领域首部涉及全类型矛盾纠纷、囊括全种类化解方式、覆盖全链条非诉流程的地方性法规。
三、从多元化解条例看沪深商事调解发展
(一)沪深商事调解发展的共同之处
沪深均鼓励开展商事调解活动、培育商事调解组织、调解员。《上海多元条例》第18条鼓励在投资、金融、房地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等领域设立专业化从事商事纠纷调解的组织,鼓励开展国际商事纠纷调解,培育商事调解服务品牌;第21条规定了调解员培训;第32条规定登记为社会服务机构、公司等的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可以收取合理费用。条例深刻反映了上海鼓励对特定行业、专业领域的矛盾纠纷进行调解,以及对商事调解品牌化建设的支持。
《深圳多元条例》以专节规定商事调解,与人民调解、劳动争议调解、行政调解并列,反映了司法行政部门推动多种调解方式全面充分协调发展。从条例第36条至第42条,对商事调解活动、商事调解组织、商事调解行业组织等作出详细规定,凸显了商事调解的规范性、市场化与保密性特征。条例第54条鼓励仲裁机构与商事调解组织建立合作交流机制,保障民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沪深多元化解条例对商事调解事业的支持,是加强两地高水平改革开放法治保障的体现,也生动反映了两地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高水平建设。
沪深均致力于健全诉调对接平台。《上海多元条例》在总则中明确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推动完善各类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条例第8-10、26、50、51、59条对诉调对接作出详细规定,由上海市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牵头建设统一的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信息化平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提供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服务;由人民法院在登记立案前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调解,或者在登记立案后或者审理过程中经当事人同意进行司法调解,进一步落实了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
《深圳多元条例》吸收了深圳法院的多项司法实践经验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条例第11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统筹协调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和诉讼之间的对接机制,第67条要求人民法院健全诉调对接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当事人选择适宜方式解决矛盾纠纷,推动司法确认等方面的有机衔接;第69、70条对法院的特邀调解活动、先行调解工作予以明确,第78条指出人民法院应当健全集诉调对接功能在内的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平台,实现纠纷分流。
沪深多元化解条例对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衔接的具体规定,是两地近年来不断推进民商事纠纷繁简分流、健全非诉解纷机制的最新成果,将进一步推动商事纠纷通过多途径实现更灵活、更高效地解决。
沪深均保障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上海多元条例》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等方面加强对接,为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提供司法保障;第53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对以金钱、有价证券为给付内容的和解协议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第54条规定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或申请出具民事调解书,明确特邀调解活动达成的调解协议纳入司法确认范围。
《深圳多元条例》第67条指出人民法院应当推动司法确认、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等方面的有机衔接;第71条规定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民事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司法确认;第72、76条进一步补充了对于具有给付内容的和解协议、调解协议,当事人还可以申请公证或支付令。
沪深多元化解条例对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可执行性的进一步完善,既呼应《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生效后对我国提高和解协议可执行性提出的新要求,也将增强商事调解的公信力,将为深圳商事调解深化发展保驾护航。
(二)上海商事调解工作独特之处
上海重视对多元解纷文化的普及。《上海多元条例》第11条指出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应当普及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法律知识,增进公众对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理解和认同,最大限度地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新闻媒体也应当组织有关公益宣传。
上海鼓励国有企业参与调解。近年来,上海市国有资产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国资委”)积极推进法治国企工作,建立部门协同机制,推动将“鼓励国企调解”条款纳入《上海多元条例》,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等签订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企业纠纷案件的多元化解决。条例第58条鼓励国有企业通过调解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且特别强调对相关人员在调解中勤勉尽责、未牟取私利的,对可能出现的损失不作负面评价。鼓励国企参与调解,将有效应对涉国企纠纷解决方式单一的问题,消除国企参与调解的困难和顾虑。
(三)深圳商事调解工作的亮点
深圳进一步奠定了商事调解全面工作的基础。《深圳多元条例》将商事调解与人民调解、劳动争议调解等并列,体现了深圳对商事调解的高度重视,提高了商事调解的地位。条例第4节通过专章详细构建了商事调解制度框架,对商事调解的适用范围、商事调解组织的登记与成立条件、市场化收费、规则报送、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导与监督、保密、行业组织等内容做了明确规定,凸显了商事调解的专业性、保密性,保障了商事调解组织的市场化运作。条例第42条肯定了商事调解组织可以依法成立行业组织,并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开展行业自律管理,是对商事调解行业自治制度的完善,为进一步培育商事调解行业打下了制度基础。深圳市商事调解协会会长丁南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深圳多元条例》创新性地规定了商事调解的行业组织职责、行业自律管理等,对促进商事调解健康有序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深圳丰富了商事调解服务内容。《深圳多元条例》创新设立了中立评估制度,条例第64、74、86条对中立评估服务作出详细规定。其中条例第64条第一款规定“矛盾纠纷当事人可以委托具有专业评估能力的专家或者其他第三方机构,就争议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处理结果进行评估”,并在该条第二、三款明确了评估报告可作为调解参考、评估的保密性;条例第74条规定调解中的评估报告、鉴定意见不违反法律规定的,经当事人同意,可以适用于仲裁、诉讼等程序;条例第86条对评估员的职业规范提出了要求,将保障“商事纠纷中立评估基地”稳步推进深圳城市法治能力现代化。此外,条例第73条将“无争议事实记载”纳入证据,规定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对无争议事实予以确认并可作证据在仲裁、诉讼等程序中提交。
深圳肯定商事调解的市场化收费。商事调解机构的市场化发展是国际趋势,也是商事调解满足社会需求的必然前提。《深圳多元条例》第38条明确规定商事调解组织可以收取调解服务费,且调解服务费用实行市场调节,收费标准由调解机构自行制定,只需报送司法行政部门。笔者认为,《深圳多元条例》的有关规定是从地方法规的层面为商事调解收费“背书”,是深圳特区打造法律服务新高地的鲜明写照。
四、对上海发展商事调解的进一步启发
无论是《上海多元条例》还是《深圳多元条例》,都是近年来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践与探索的集大成者。两者各有侧重,《深圳多元条例》作为国内商事调解领域最新立法,深刻反映了深圳在商事调解建设中的多样创新,对上海发展商事调解、提升法治城市现代化有较多启发。
上海应进一步抬高商事调解地位。当前《上海多元条例》只是鼓励商事调解发展,虽然在大调解格局中提出了“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的概念,但难以完全囊括商事调解。今后对《上海多元条例》的完善有必要对商事调解以专章规定,对商事调解机构、商事调解员、商事调解服务作出规范性指引,抬高商事调解在大调解格局中的地位,对商事调解提出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的要求,为培育商事调解服务市场提供立法支持与顶层设计,满足日益增长的解纷需求。
上海可探索丰富商事调解行业建设。深圳调解协会的成立和中立评估服务的创设为我们丰富商事调解行业建设提供借鉴。《上海多元条例》规定了大调解格局下的调解行业协会,为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立上海商事调解行业协会提供了可能。上海已经有一批从事商事纠纷调解的组织,为了更好地统筹协调各类商事调解服务,提升各商事调解机构的能级,有必要设立上海商事调解协会,推进上海商事调解服务的整合。早在2017年9月,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就启动金融消费纠纷中立评估机制,构建了“投诉+调解+裁断”一站式矛盾化解平台,上海可考虑升级中立评估服务以助推商事调解。
上海应进一步出台鼓励国企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实施细则。“鼓励国企调解”条款是《上海多元条例》的一大特色,有着积极意义。在《关于推进法治国企建设加强法律案件管理的实施方案(2020-2022年)》中,上海市国资委提出要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具体举措包括与相关单位建立合作机制、组织系统内企业纠纷协调、运用社会调解、自行和解等多种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为进一步发挥商事调解在涉国企纠纷中的作用,上海可以通过《上海多元条例》实施细则的形式对国企参与多元解纷的方方面面予以细化,为国企参与商事调解提供规范指引,助力上海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顾伟强:《关于<上海市促进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草案)>的说明》,载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第二号),http://www.spcsc.sh.cn/n8347/n8407/n9002/u1ai236425.html,2022年5月27日访问。
[2]余东明、黄浩栋:《“云解纷”隔空就地化解矛盾纠纷,上海法院打造线上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载澎湃号——上海市司法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165736,2022年5月27日访问。
[3]余东明、黄浩栋:《上海浦东法院组合拳力克“多大难新”》,载法治日报2021年7月19日,第1版。
[4]张玮玮、潘辉:《先行先试打造商事调解“深圳样本”,创新路径优化营商环境》,载深圳商报,2021年12月17日。
[5]蓝海现代法律:《全国首个商事调解协会在深揭牌成立》,载法治网,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21-05/23/content_8512405.htm,2022年5月20日访问。
[6]杨溢子:《城市“法治力”满格 治理现代化突围》,载南方日报,https://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2204/18/c6411758.html,2022年5月20日访问。
[7]邓子良、丰雷:《多项司法实践经验被采纳,深圳中院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贡献法治力量》,载南方报业南方+客户端,https://www.163.com/dy/article/H5E5VANH055004XG.html,2022年5月27日访问。
[8]上海市法规局:《上海市国资委推进法治国企建设的实践与探索》,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http://www.sasac.gov.cn/n4470048/n16518962/n20648677/n20648722/c23594214/content.html,2022年5月27日访问。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滨江大道2525弄5号A幢
电话:+86 21 50151868
Email:info@scmc.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