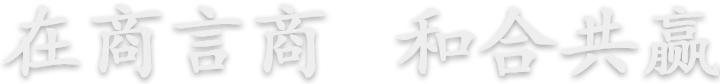
将生态文明理念和调解先行作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的信条
当前在一带一路项目中,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巨大的文化差异、社会体制差异、生态系统差异以及相关的法律和当地监管要求差异。“生态文明”理念的本质就是承认广泛的源于各地文化的规范和习俗,体现了对文化和生态多样性的包容态度。
“生态文明”理念源于儒家和道家的古典哲学理念 – 尊重自然,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平等性、维持社会内部、自然内部的和谐以及维持社会与自然间的和谐。 儒家倡导“天人合一”,即天与人的关系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相通和统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主张“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即夏秋冬按天时运行,万物因而生息循环,不受人的干扰。荀子亦主张‘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即大自然的运行有其自身规律,这个规律不会因为三皇五帝尧的圣明或者夏朝桀的暴虐而改变。道家主张“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即用自然的常理来看,万物本没有贵贱的区别,皆为平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味着人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在大地上生存,应当遵守大地万物生长作息的规则,整个大自然才能维持动态平衡。
通过利用比法律更广范的规范性原则来强调对“平衡”和“和谐”的维持,“生态文明”的原则可以作为解决一带一路中环境争端或通过调解或裁决性手段可能产生环境影响的争端的概念性框架,可以作为关注和解决任何可能在商事争端中被忽略的环境因素考量的安全阀。“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追求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存在于多种不同文化,几乎得到全球范围的广泛承认。例如,佛教认为,可持续性涉及生态、经济和可进化性,即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潜力;印度教强调人类自身与地球上每一个存在的统一性;《古兰经》多次提到水和其他重要自然资源,为保护和公平分配这些资源制定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当前解决争端的裁决性手段主要包括仲裁和诉讼。全球几乎每个国家都加入了《纽约公约》,这使得在一个司法管辖区作出的仲裁裁决在另一个司法管辖区能够得以执行。但是,当某争端带有跨国界和跨文化的性质时,这种裁决性质的国际争端解决方式既受到程序的限制,也受到成文法所涉法律关系有限的限制。它们所需投入的金钱和时间巨大,而且由于各主体的资金实力悬殊问题,往往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而且这种裁决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往往是敌对性的,这会影响将来商业关系的保持和继续。同时,对于争端解决的整体思路和进程将完全被握在仲裁庭手中,争端双方无法对争端解决的过程和结果有所掌控。而在现实操作中,尽管有《纽约公约》,但是这种“不是赢就是输”的争端解决方式也带来了执行上的挑战。
而调解,作为一个有第三方中立者参与的争端解决手段,应当被鼓励作为解决一带一路争端的首要“第一线”争端解决工具。因为调解是一个促进式而非裁决性的过程,调解一般在一名开明的调解员的引导下进行,该调解员接受过多利益相关者环境纠纷解决的调解技术训练,他能够通过在调解程序开端进行有针对性的声明、利用纳入“生态文明”理念的调解规则、争端各方对生态文明概念作出预先承诺等方式,鼓励争议双方以与“生态文明”原则一致的方式解决争端,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也能够保证尊重和考虑争端双方文化背景下的“活法”。调解员会利用大量技巧来促进双方的共同理解。
调解有两种形式 – 辅助型调解和评估型调解。在评估型调解中,调解员有权向争端双方就争端解决方案提出建议。调解是争端双方自愿进行的过程,也是全程保密的,同时争端双方对处理结果有完全的掌控。
需要强调的是,随着《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推出,中国、美国和印度作为全球巨头已经加入该公约,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也已签署该公约,这提供了一个在签署国执行所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有效机制。因此,《新加坡调解公约》可以说是将调解提升到一带一路沿线争端解决的主要手段的催化剂。
就一带一路项目开展以来,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东道国之间不断产生争端,这些争端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多为不同文化背景、当地生态文化体系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当地惯例综合导致的误解。例如,华坚集团在埃塞俄比亚投资的工厂聘用了埃塞俄比亚当地的员工,但是由于埃塞俄比亚与中国的文化差异、贫富差距、卫生习惯、生活理念的不同,当地员工不时进行罢工,导致华坚迟延交货并且生产的产品质量也不过关。此外,根据中国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9年度一带一路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60.9%的在印尼投资的中国企业、63.6%的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的中国企业和50%的在马来西亚投资的中国企业在接受调查时表示,宗教信仰以及中国管理层和当地员工之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差异严重影响了他们企业的当地运营。这些都不是单纯可以靠法律去解决的矛盾,而是需要利用当地惯例、文化习惯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去解决,因此,一个有效的可以利用纸面法律以外的“软法”的争端解决机制尤为重要。
此外,相较于纯裁决型的争端解决手段,调解能够带来更多的重要价值,因为它将社会规则纳入争端解决的体系中,使其成为争端解决的重要部分,这些社会规则就包括环境保护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在跨文化的语境下,特别是BIRCH所描述的相对于“低语境”而言的“高语境”中,调解能够极为有效地解决争端,因为争端往往产生于错误认识、错误沟通和错误的理解。正如BELHORNE (footnote?) 所指出的,当争端方有互惠关系且拥有共同目标时,他们将更加适应最佳社会规范,时间限制和非正式性能够促进结果的达成。调解平台能够满足这些争端方的需要,调解员努力恢复争端双方的信任,在这样的前提下将更有可能产生公平且富有创造性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会将环境影响纳入考量而且可能会与裁决型争端解决手段产生的结果大相径庭。因此,尽管仍然需要在国际公约中被确立或者在争端适用的合同中被要求,“生态文明”的原则仍然可以影响争端双方所达成的调解协议,该等原则将在一位调解员的引导下,作为适用的“活法”的渊源之一被争端双方承认与认可。
当前,已经有很多争端解决机构提供利用国际调解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由于调解的自愿性质,对于调解的选择最终取决于争端双方的意愿。可供选择的机构包括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设立的“一站式”国际商事多元纠纷解决平台,争端方可在此从一套标准程序和配套机构中选择他们倾向的争端解决工具、国际商会及其专门的国家替代争议解决中心以及“一带一路”委员会、新加坡调解中心设立的调解平台以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联合的各机构,包括与欧盟知识产权局共创的中欧知识产权联合调解机制以及与美国司法仲裁调解服务公司共建的中美国际商事联合调解机制、海牙常设法院下设的环境和自然资源纠纷调解规则,以及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待发布的调解规则。
总结而言,在深谙如何利用文化语境并且对环境考量了然于胸的调解员的引导下,争端可以在一种兼顾文化与生态因素的方式下得以解决,并且达成一种在传统裁决型争端解决模式下由于种种严格限制而不能达成的争端解决方案。争端双方有机会对其争端的解决方案行使控制,也可以在形成此类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自由表达是否愿意接受所有类型的“活法”,例如商事习惯法和可持续理念。长此以往,将能产生更高更快的争端解决率,更高的争端双方满意率,且最终达成更高的争端方参与率。
Elizabeth BIRCH, “Pract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Mediation(从实践和文化角度看国际仲裁)”, 《国际仲裁年鉴》, 5, 2017, 215–234, 第229–232页.
Scott R. BELHORNE, ‘Settling Beyond the Shadow of the Law: How Mediation Can Make the Most of Social Norms(走出法律的阴影:调解如何充分发挥社会规范的作用)’, 《俄亥俄州纠纷解决杂志》, Vol. 20: 3, 2005, 第988页.
Full 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Volune 4, Issue 2, December 10, 2020.
作者:
孔宏德,美国德汇律师事务所上海办事处管理合伙人,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能源与环境专委会主任、调解员,纽约大学全球客座教授,上海国际仲裁委员会和深圳国际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欧盟商会上海环境工作小组主席
朱雪玮,海问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律师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滨江大道2525弄5号A幢
电话:+86 21 50151868
Email:info@scmc.org.cn


